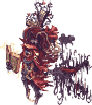|
    
 
 我们约会吧! 我们约会吧!
|
【五月征文】城爱
城爱
借以此文,赠与相爱七年的某孩子和清央。
你们教会我,对彼此仁慈。
【酉锦】
这座城市,终有个人将会爱你。
就像你爱这座城市一般。循序渐进。因果相关。
寒鸦在离开这座城市前,俯在我的耳旁,轻缓而温柔地说道。
于是四日后,寒鸦背着他巨大的行李包裹,彻底消匿在铁路站台。
他说,酉锦,我要去寻找,一座爱我的城市。那将是属于我的。
那刻,寒鸦勇敢而坚强地如同一名战士。怀揣着莫大的志愿,踏上征途。
而我所处于的城市,它是被孤立的,带着抑郁和憧憬。
寒鸦形容它,部分繁华,部分僻静。性格独立,彼此隔膜。如同巨大溃烂伤口,随时吞没情感而崩溃。
我知道,寒鸦并不喜爱它。但,并不厌倦。关系模糊而微妙,彼此牵引着一条线,挣扎而缠绵。
几乎所有人都以为,寒鸦喜欢我。他习惯拉着我的衣角,在他的掌控范围下,大声说话,语态暧昧。
可我知道,寒鸦喜爱的人很独特。独特得,几乎特立独行。
寒鸦是同性恋,而他喜爱的则是,一个雌雄同体的孩子。这是秘密。
他说,女人很下贱,男人很愚昧,而不男不女最为无知。于是,只留下雌雄同体可以让人喜爱。
那日寒鸦拖着我逃课,我们在小小的隔间钢琴室,说着话,用力地奏出不同怪异的声响。彼此和谐。
随后寒鸦跻身到我身旁,凑近说,来来来。酉锦,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
【寒鸦】
我叫寒鸦。由爷爷钟爱秦观的“寒鸦万点,流水绕孤村。”而来。
酉锦说,寒鸦,你注定是被孤立存活的懦弱勇士。孤村环绕。
我不知道,我为何要告诉酉锦,我是同性恋这件事。这并非秘密,而是禁忌。
只是那日,突然想起,就这般随口说了。
我靠着酉锦的左边,俯在她的耳垂旁,轻声地说,酉锦,你知道吗,我是同性恋。而我爱的人则是,雌雄同体。她的耳垂微微有些泛红,很是可爱。
然后,酉锦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说,恩,我知道了。寒鸦。
这便是酉锦,唯一让我并不排斥的女性。一个妄图对一切漠不关心真性情的女子。
末了她缓缓道,寒鸦,你只不过厌恶女子甚过男子罢了。我哑然,烟燃到尽头,火星串动。
逃课当日傍晚,父亲被请去办公室。这个试图让自己显现平静绅士风度的男人,死死握拳不放,面色微红。
老师轻咳,打破尴尬说,寒鸦,请你说说,今天下午你带着酉锦去了哪里。
我默不作声地转头看酉锦,她依旧低着头,神情内敛而害羞地藏在角落。
父亲深吸一息,略带沙哑道,寒鸦,你说,你到底做什么去了。我似乎已听见他手指关节在咯咯作响。他依旧如此容易动怒与急躁。
老师尴尬地陪笑说,寒鸦爸爸,不要生气。好好问孩子。如此云云。
那个男人抬头愤恨地直视我,道。寒鸦,你到底想怎样。声音咬牙切齿地生硬。
老师,下午我突然胃痛,让寒鸦陪我去了次医院。病假单明天给你,行吗。声音有些唯唯诺诺地轻柔。我转头看酉锦,她抬起头,略微苍白的脸上,隐有疲倦。
老师对于这并无预知的答案而一愣,转而温柔而关怀道,酉锦,怎么会突然胃痛的呢。可按时吃早饭?怎么会这么不小心。这样吧,那篇学习小结你,缓两天周五再交好了。还有别忘了,傲准备下个月的竞赛。
于是,一场闹剧就这般不了了之。或许,还坏了那些看乐子的兴致。
从办公室出来,我掏出口袋里的烟和打火机,刚欲点上。父亲从我身后,狠狠地夺取,然后扔在地上,愤恨地踩烂,便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开。我看了看一地破碎,转头对酉锦道,你说,他将有多恨我。
母亲常无奈说,寒鸦,你不要憎恶你的父亲。他只不过愿你如寻常般健康生活。我拂去母亲的手,笑着说,我从未憎恶任何人。只是厌恶。
我没有理由憎恨他人。就如我没有理由喜爱他人一般。
如若寻常包括同性爱恋,想必父亲会待我稍许温善仁慈些。或许,更像个父亲,也说不定。
酉锦道,寒鸦,我要回家了。她依旧苍白的脸颊上,带着狡黠的微笑。
我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,道,酉锦,我未曾发觉,作为一个优等生,连说谎都有优先权。
暮夏夕阳。
酉锦说,寒鸦,我们已在灭绝的尽头。
这句话,如同藤蔓般,就这样从她的口中爬满了我的内心,贯穿疼痛。那是链接我们彼此的,唯一的桥梁。
【酉锦】
我的胃很痛。胃酸使我幻觉自己存活在一个被硫酸腐化的国度,带着恶臭。
在办公室里,第一次看见寒鸦的父亲,那个与寒鸦生存方式格格不入的中年男子,严谨而强势。同寒鸦一般的固执不化及性情落拓。
我就这般望着他,从一开始到结束,他无时无刻地,死死地,注视着寒鸦。
无时无刻。愤愤地,无奈地,甚至丝毫的溺爱地,注视着。
寒鸦从不知道,他只是自顾自地仰着头,固执面对天花板的玻璃,独自嘲笑。无论如何,他的父亲给予他的是,完整而真实的情感。寒鸦他不欠任何人,即使仇恨,那亦是属于他的。
回到家的时候,家里一片清冷,如同冰窟般,毫无生气。桌上放着五十元和一张便条。
酉锦,记得一个人买晚饭吃。切勿空腹。
我厌倦地将纸条撕成碎片,揉进垃圾箱。径直回房,锁门。我的胃,疼痛在空荡的房间,留下此起彼伏的回声。
从出生开始,便被浸没在这般的淡漠清冷之中。它如同一条源远而长的河流,通向未知的陌路。
我恨我的母亲。我恨我的父亲。
但这般情感,却从未有过般,不真实以及虚无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
是不是,所谓虚情假意也不过如此。
寒鸦嘲弄道,酉锦,你这是典型的装逼。
我是难产的孩子。据说,在还是四个月的时候,就被医生劝说,需要留院观察。
母亲有先天性心脏病,并不适宜怀孕。但她依旧坚持。她对父亲说,她想生下这个孩子,让他来替代自己。
她的执拗使父亲最终妥协,并且最终带来悲剧。
以至于,后来父亲常说,酉锦。记住,至少你要为你的母亲活下去。
这句话的潜台词是,酉锦,你没有资格肆意地荒废你的生命。那本不是你的。
所有人都说,酉锦,你看,你的母亲如此疼爱你。不惜与自己相抵。而这个时候,父亲总会站在我身旁,眼神迷茫而徘徊地看向我。
他爱我,仅仅因为我作为母亲的衍生替代品而得以存活于世。
他亦恨我,是我的诞生而执意夺取他心爱女子的性命。
而我恨他们。那是如此庞大的阴影,它笼罩着我几乎所有行迹,时刻提醒着我,这个生命还附加着另一意志。我需要善待它,异常小心地。
他们不应该将我生育出来的。这是个错误,无法弥补的天大漏洞。
我不稀罕这施舍交换。那般无私使我更为自卑及无地自容。
寒鸦说,酉锦,你妄想漠不关心的活下去。你可知,你到底爱什么,以及需求什么。
深夜十一点半。房门开启,然后合闭。声音轻缓。他走至我的门前,停留许久,然后默不作声的叹声离去。
于是,一日复去。
寒鸦说。酉锦。我是个同性恋者。十四岁,与男伴在街角长椅亲吻,被父亲撞见。便彻底打碎他培育儿子的教育梦想。
他说,酉锦,你相信吗。那日我竟恍惚听见,玻璃下坠被击碎的声音。我破碎了他的梦想,他击破了我的幻觉。其实我们谁都不亏欠谁。真的。
【寒鸦】
他们在争吵。或者说,他们在战斗,用一种清冷而淡漠的方式。
我在楼道口,抽着烟,等酉锦。
他说,酉锦,把蛋吃了。她说,恩。
他说,酉锦,把蛋吃了。声音微怒。她说,恩。声音平静。
他说,酉锦,把蛋吃了。然后,门开了。酉锦拿着书包,跑到我的面前。说,寒鸦,我们走吧。
我转头,他冲至门口,将白煮蛋硬生生地塞在酉锦的手中,道,酉锦,你给我把蛋吃了。你不要忘了,你至少要为了你母亲而珍惜自己。
酉锦道,不要提我母亲。既然如此,那就应让她活下去。而抹杀我。随而她拉着我,奔跑离开狭窄昏暗的楼道。天色燥热,我的手心溢满了汗渍。
寒鸦,我还活着吗。她抢过我的烟,放在自己的唇上。烟呛着她,不断咳嗽。这是她第一次抽烟。
我夺回我的烟,仰头道。酉锦。这座城市是个巨大的伤口,我们终究会被溃烂吞噬。尖耸的高楼,刺破天际,天色氤氲。
我学过,油画,素描,书法,钢琴。初二前,成绩斐然。
父亲愤恨地说,寒鸦,你看,你曾让我如此荣耀与骄傲。
十二岁,隔壁班某个不记得名字的女孩,突然站在我面前,面色羞愧而别扭地低着头,阻拦我在路边。
我环臂默默地望着她,她的窘迫,无助,羞涩,像是被揭去了透明面具般,皆表于象。
良久,一个声音终打破沉默。她说,寒鸦,我可以喜欢你吗。她将头藏在更深的阴影中,浑身颤抖。
我看着她霎时通红的耳根,无法忍耐地扶着腹部,自顾自地,毫无收敛地,大笑起来。哈哈哈哈哈。
喜欢我?废话,这是多么装逼的废话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自以为是的掌控他人。真他妈虚伪的让人厌恶。
似乎是从那句话开始,我发现,我厌恶女性。这样的愤世嫉俗竟然暗藏在我的身体里整整十二年后,开始苏醒长大,如同疯狂的种子,猛烈地冲击我的所有认知,击破幻觉。
十四岁,我认识了隐时。他摇着啤酒瓶地凑到我耳旁,对我说,寒鸦,我他妈的喜欢上你了。
于是,我便成为了同性恋。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情。我们在街上亲吻拥抱,甜言蜜语。像足了无所事事的痞子。
十六岁,隐时说,寒鸦,你不要妄想把我当作,你对这座城市的报复。然后彻底销声匿迹。
其间,我未曾尝试寻找。我是自怜自爱的冷漠小丑,而他亦。却忘却了我们不是彼此的影子。
十八岁,酉锦说,寒鸦,你对这座城市的恨是与生俱来的。无人可以消除。
姑姑打电话说,寒鸦,来北方城市吧。你需要重新开始。
父亲说,你给我滚,寒鸦。有多远滚多远。
酉锦说,寒鸦,我发觉,原来我一直爱着这座城市。
那夜,我梦见酉锦。我躺在她的怀中,犹如婴孩般屈卷姿态。
她如同墨迹般的长发,落在脸庞,痒痒的。
许久,她俯下亲吻我的眼眸,道,再见,寒鸦。
【酉锦】
寒鸦说,酉锦,我将离开这座城市。
寒鸦说,酉锦,为什么你始终不愿和我一起离开。
你到底爱这座城市什么。
父亲说,酉锦,我愿送你去英国读书。或许这般,我们可以淡漠地彼此依存。
我一而再地摇头,直至深感,脑中晃荡得只剩空白。
他说,酉锦,我不知该如何来关爱你。对不起。
你到底爱这座城市什么。
我爱这座城市什么。如此执迷不悔。
一岁。他指着灰白照片对我说,酉锦,你需要记住,你的所有都是这个女人给你的。
三岁。我首先学会的汉字,是母亲和她的名字,善柯。他说,酉锦在纸上各写两百遍。
五岁。他为我讲述所有有关善柯的事物。喜爱的,憎恶的。在临睡前,不厌其烦地叙说他自编自导的童话。一遍再一遍。
七岁。在入学前那夜。他说,酉锦,我不许你擅自糟践你的人生,你没有权利。这是场开始。你必须记住。你是为了你母亲而存活的。
十岁。他将我搂在怀中,眼泪沾布颈项。他的胡子渣抵在我的锁骨,咽唔道,酉锦,她离开已然十年。酉锦,我如斯想她。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
十二岁。他将我锁在门外,整整一夜。他拿着我五十七分的物理卷子,歇斯里底地说,酉锦,你看看,你到底学了点什么。这样你怎么对得起你母亲。
十五岁。我的生活里,布满了,母亲,善柯,她,这些字眼。密密麻麻,透不过气。
十七岁。地理生物重考。物理化学数学满分。我挑衅地看着他,他默不作声地抽回成绩单,独自回房。我彻底走上与决然她相悖的道路。
十八岁。他说。酉锦,一切都是我的偏激错误,请不要憎恶她。
这座城市处处充斥着她的味道。她喜爱的花开满了街道旁的草坪,而我踩踏着学会走路。
她第一次结识父亲的地方在学校的拐口,我时常咬着冰淇淋若无其事地走过。
我在她就读小学的地方读小学,就读初中的地方读初中,就读高中的地方读高中。在她领奖的讲台处,拿着各式的奖状,对着相继假装欢愉。在每个用过的课桌内板的角落上写,善柯和酉锦。
她依存欲这座城市,整整一世。而我将依存在她的身上,亦是整整一世。
我自知,她很爱我。可是,她只能如此爱我。就如我只能这般恨她一样。
我们惟独缺失时间来彼此维系。那些冗繁的情感纠缠被淡漠在年华下,我不再给她机会来深爱我,而她亦不曾给我契机来憎恶她。
于是潜移默化地爱上这座城市。这里,曾经住着一个深爱我而被我憎恶的可爱女子。
父亲说,酉锦,你母亲曾说,这座城市是她唯一的归宿。她是属于这里的。
十一月。寒鸦奔赴北方B城。
临行前,寒鸦坐在站台的栏杆上,说,酉锦,有时候,我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改变宿命,就如现在。
他说,酉锦,你可相信,一切能重新开始。
火车将开,列车员拿着喇叭徘徊在站台,不耐烦地喊着。我低着头,看着满地烟蒂。
寒鸦笑了笑跳起身提起行李,揉乱我的短发,道,酉锦,你可以蓄起长发了。
我轻念,再见,寒鸦。再见,寒鸦。再见,寒。鸦。
他转头,对我说,酉锦,再见。
寒鸦说,酉锦,我要去寻找一座城市,一座爱我的城市。那将是属于我的。
我异常坚信他将不离不弃地寻找这样一座城市,一座为他带来新生,足以让他爱的城市。
我们同是与城市恋爱的孩子,在此深陷不出。
火车缓慢地加速行驶。那将通向何处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全文完。[/COLOR] |
|